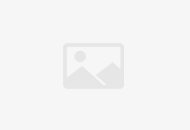陈宇有两种身份——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50亿票房背后的原创剧本·编剧。
从讲台走入市场,由实操反哺理论,学界和业界的双重视角,在他这里形成了彼此滋养的良性互动。
在他身上,看不到沉溺于自我表达的学院派通病,又比市场投机者多了一份审慎的反思和更为长远的艺术追求——
以新鲜独到的叙事方式,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身上,挖掘大多数中国人抱持的价值观。
时间、空间的极度限制所产生的极致张力,让我们久违地感受到叙事本身的魅力。
第二次与陈宇聊电影,聊创作。
也又一次听他强调——故事,是电影的本体所在。
只有故事讲好了,所有其他的表达才有机会抵达观众。
他说这话,有充足的底气。
《狙击手》《满江红》两颗惊雷炸响之后,陈宇无疑成为当下中国电影最抢眼的原创势力。
其中,《满江红》讲故事的技巧和效率,现在回想依然惊人。
无论是将“三一律”做到极致的故事,还是饱满鲜活的小人物群像,以及那一个个起到多重功能的“局部设计”。
何立的诡刃、秦桧的“乌鸦”、小女孩手里的樱桃,帧帧耐嚼,回味无穷。
当我们看到那一抹肃杀中的沁红,会既喜又悲,继而感受到力量时,就正应了他所说的——
“电影实际上是创作者和观众的共谋。”
不是单向一时的输出,银幕上下双向的交流才更隽永。
在采访中,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
陈宇对优质故事近乎痴迷,但是对“写”的过程完全祛魅。
他给青年创作者一个忠告:每天都要写。哪怕写得很坏,先写50万字再说。
量变引起质变,成熟的作品一定脱胎于长期稳定的训练。
“你要把它视作一种职业,而不是平时的某种情绪的出口。”
他认为电影最终应该抵达价值观与情感的共鸣,而通道是由实证主义所搭建的精密机关。
欢笑或落泪的感染力背后,是创作中的三一律、倒推、升维理论……在共同奏效。
陈宇不信任神秘主义的灵感,只依赖可重复的工作方法论。
他不认为有伟大的作品,只有特定环境下最恰当的作品。
他不鼓励年轻人过度关注自我风格,而要去与时代和普通人接壤。
对于讲故事这门手艺,陈宇既是年轻学子的导师,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学徒。
从亚里士多德到希区柯克,从司马迁到曹雪芹,这些国内外的先贤大师们无不是追寻有效的讲故事的方法——他依然在这条探索的路上。
当然,陈宇也有想做普通观众的时候。
最大的放松方式,就是不带专业眼光地追剧。
谈及最近讨论度颇高的网剧,陈宇对《黑暗荣耀》和《漫长的季节》很是欣赏。
尽管说着说着,又忍不住分析起韩国影视工业体系和国产剧的非线性叙事冒险来……
目前,陈宇正着手准备一部关于草根青年的青春片。
在爱情几乎霸占国产青春片所有注脚的情况下,陈宇认为,青春片的核心在于成长。
他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行使青春片这一类型的真正使命——给当下年轻人以勇气和抚慰。
“因为今天的年轻人确实不容易。”
给与年轻人理解和支持,替他们说出话来,是陈宇接下来创作的重要目标。
我无比期待,一场与你我青春的共谋。
以下,是陈宇的部分采访内容。
院长:您还有没有想过更极致的故事?比如说真正的密室或者是设置更短的时间。
陈宇:有过。每一届学生我都会有这样的题目要求,比如说我会让他们写一个场景,在一个公园里有张长椅,镜头对着这张长椅,然后从东边来了个人,从西边来了个人。这两人在这个长椅相遇,从这开始要演20分钟,中间必须包含几个转折,叙事的趣味性,三个以上的叙事层次,然后这20 分钟不能让观众离去,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极致训练。但在一部电影中我是不是要去追求这种极致的形式感?倒不一定,这个我觉得是一种能力的开掘,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对叙事技能和叙事规律的能力的培养。当然这种形态有时候也会比较有效,包括我们后面也会开发类似于这样的项目,可能更为极致的三一律,也是有可能的。
院长:前几年很多国外的片子流行拍摄类似题材,比如有一部电影就完全发生在面试的房间里(《终极面试》)。
陈宇:《彗星来的那一夜》《来电狂响》。
《彗星来的那一夜》剧照
院长:对,不过好像国内拍的比较少。这样的故事很难写吗?
陈宇:它对于叙事要求是比较高的,你不能让观众走神,不能让他腻,你不能利用其他所有的元素包括空间转换、变化镜头等各种手段去丰富影像的吸引力。全靠你的设计,全靠你的cut,全靠你的调度。
院长:国产悬疑电影成功的也不是特别多,而且这几年大部分都是翻拍作品。
陈宇:对,这两年我们也对悬疑比较感兴趣,主要的原因是我倾向于创作那种充分能体现叙事魅力和价值的影片,本身这个故事讲法上面就能让观众深深地吸引进去。而悬疑类影片它就有这样的特征。
院长:观众看的时候大多关心的是反转,最后的反转会不会很惊人,能不能让我猜不到……您在写的时候,反转是不是最难的?
陈宇:我自己有一个理论叫做升维理论。凶手是a还是b?我把它叫作翻烙饼式的反转,同一维度的反转实际上是比较容易想的。而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反转是从a到b以后,这个事态的维度产生了变化。比如说a是一个争夺钱财的斗争,反转到b的时候发现压根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复仇,它就升了一个维度。这个反转我认为是有效的,也是一种好的反转。然后从b最后升到c的时候,他可能又升级到了国家大义的层面。《满江红》里面的反转,我是尽量做成从那种简单的翻烙饼变成一种对更深度信息的挖掘。
院长:观众也是从追求一个结果,达到了一个情感上的共鸣。
陈宇:对,像悬疑片,似乎是在跟观众在做一场良性的智力较量,一种合作式的较量,但是最后我觉得还是要指向一种价值观,指向一种情感的抒发和表达。
院长:前几年我们一直在说,大家好像看电影特别重情绪,我觉得这两年大家更加重视故事和叙事,从电影和电视剧上都有这种现象,您有类似的观察吗?
陈宇:就是简单来说,观众更重视从故事中获得的乐趣和价值。这个我觉得确实有这么一个趋势,而且我是为这种趋势感到欣喜的。就是它实际上是市场的深化、系统化、完善化的一种体现。它更多地是说,我看你这部电影、这俩小时的故事能够得到心理和情感的满足,然后我再去审视你的命题和主题,审视你的价值观是否能够和我的心灵所契合,那个东西是否能够让我感到冲击和震撼。这两个东西它缺一不可。因为电影本质上是一个讲故事的艺术形式,故事讲好了那个价值观的东西才能够到达观众。所以这是一种对电影本体的回归,我也把它视作一种返璞归真。
院长:那关于强叙事型的创作,您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吗?看《狙击手》和《满江红》的时候,我觉得跟张艺谋导演之前的电影比,它有特别多戏剧化的元素在里面。
陈宇:对,当然就是我有自己创作故事的一套方法论,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叙事原理的系统化认知,比如说电影的叙事第一性原则。我刚才讲到电影第一个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讲一个优秀的故事,然后也包含一个故事是如何传递给观众的。另外你刚谈到艺谋导演的创作有所波动,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在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时代命题和时代趣味的发展,在不断更新迭代艺术观念的一种体现。我觉得这个特别值得我尊重,而我也很乐于也很高兴能够参与到艺谋导演他自身的这种变化之中,我也贡献我自己的力量,而且他的观念也是和我非常契合的。
我不把自己的第一身份视作电影人,我的第一身份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只是用电影这种方式在讲故事。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席勒也好,到希区柯克也好,包括我们中国的司马迁、施耐庵、曹雪芹、汤显祖也好,都是不断寻求一种有效的讲故事的方法。所以我也在继续学习这些先贤大师们的创作,然后也在做自己的思考,如何用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讲述一个优质的故事去传递给观众,这个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院长:对于比较年轻的创作者来说,您觉得是直接上手比较重要,还是先把这些都研究透比较重要?
陈宇:天下没有一蹴而就的事,不太可能把所有的武艺都学到身,像武侠小说里面那么理想化——突然有一天师父说,“好,你已经全学完了,你现在可以下山了”,这个不太可能。当然也不可能是说,“行,你在江湖上且混着吧,江湖逐渐地你就懂了”。
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你要有理论基础,同时也要在中间不断去提升你的认知。我在大学里作为研究者,能让我有一个审慎的态度去进行规律化的总结,进行理论上的提升,那同时这个提升能够用在创作的作品之中;同时在产业里面的工作,它能够很务实地返回到这个理论的认知中间。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我这儿还是非常良性的。所以一个年轻创作者,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分别去补这两方面的东西。但是总体上他不太可能完成两匹马齐头并进的情况,大部分情况是交错着往前推进,这可能是一个常态。
院长:您在多次采访中说过不太相信灵感一说,比较像建筑师一点一点扎实地把剧本搭出来。但我很好奇,您真的就没有神来一笔,突然想到一个点子的时候吗?
陈宇:我不是不相信,我希望依赖灵感,但是主要是依赖不了。你既然叫灵感,就是说它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的东西,但是你作为一个职业工作者,你要在恰当的时间交出恰当的作品。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去依赖一个你不可依赖的东西?所以说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能。包括在我跟我们团队和学生的交流之中,我的态度就是:你依靠灵感那就完了。在我看来,一个有效的、实证主义的、精准的工作方法论下,做出那个时间点,那个环境下,那个市场中最准确的作品才是恰当的。所以说我的观念是没有great,只有perfect。只有最恰当的,没有什么泛泛意义上的伟大的作品。比如卓别林《寻子遇仙记》这样的作品,现在再看,我们都猜到后面是啥,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它就是最准确的作品,也是最优秀的作品。
因为电影这个东西它特别依赖于环境,你和观众之间的交流,就特别依赖于对外部这些环境和条件的判断,而不能说是刻舟求剑式的——反正我这个东西就是很伟大。倒不是很功利地说那就等于卖不着钱,而是你失去了和观众共同完成一个优质作品的机会。我认为电影实际上是创作者和观众的共谋,如果没有形成双向的交流和共谋的话,仅仅是从一个人的某种情绪和情感出发,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它是有问题的。
院长:您目前的创作里大多以小人物为主角。大时代之下的小人物,观众是最容易产生共鸣的。但是我也很好奇,您有没有想过创作一个我们都知道的所谓的大人物的故事?
陈宇:首先我认为电影就是讲个体的,哪怕它是一种典型的个体,比如《狙击手》,它写了一个志愿军战士,似乎是一个群体的体现,但它落实到影像中间,落实到这个具体的故事中间,它还是一个个人,他有他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他的习惯、他的缺陷,有他最惦记的事情、最恐惧的事情。我觉得电影本质上是在写每一个个体的情感,而不是在写群体和人作为社会学式的、论文式的总结。
社会学总结就正好相反,哪怕写一个快递员,本质上一定是在写他们的共性,他们这个群体在社会上的位置,以及经济和文化的这种位置。但是这个就是写论文,这不是我们作为文艺作品所代表的事,而文艺作品恰恰是在共性的基础上,要写这个人的个体的情感、个体的命运,个体的感受。第二个就是说,即便我们要写一个众所皆知的人,比如写岳飞,写李清照,写苏轼,我觉得也应该挖掘还原成一个人,而不应该只去写他在我们大众心中的那个标准样态。因为标准样态实际上已经是抽象出一些特质了,那个抽象出来的特质,就离这个人越来越远,我们要把那个特质抓住,但是你最终还是一个人。我认为这是叙事艺术应该干的事,而不是去写一篇论文,写一个历史。
院长:您平时的创作环境是怎么样的?会有专门一个时间,专门就在一个地方去写剧本吗?
陈宇:我其实很普通的,也没什么特殊的癖好。给有志于做创作的小伙伴的忠告是,我自己也在努力往上面走——如果你想做一个职业创作者的话,那你就每天都要写。首先我比较认同史蒂芬·金的观念,每天都要写 3000 字,哪怕第二天全部推翻也要完成这个工作。史蒂芬·金说他只有两次没有达到——一次是他出了重大车祸差点死了,另外一次是他结婚那天。当然我不太相信他这块哈哈哈,但这种作为职业创作者的做法和观念我很认同。你要把它视作一种职业,而不是视作平时的某种情绪的出口。
院长:对,我自己也能发现,一旦松懈下来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再进入会比较难。
陈宇:有好多人说,唉呦,我写了个好东西。我就会先问他一句话:你开始工作以来,你一共写过多少字?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说你没有50万字、100万字打底,其实很难出现一个成熟的作品。你不管怎么写,哪怕你写得很不好,50 万字先写了再说。一旦当你写到一个总量的时候,你的水平就会自然地超越大路货了。
院长:您业余时间有自己的放松方式吗?
陈宇:看新片,既是工作也是放松的方式,我往往会不带着专业思维看新片,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娱乐。我觉得像一个普通观众那样去看电影很重要。Sense 很重要,否则的话,你会慢慢地不像一个普通观众,那个是很可怕的。
院长:这两年网剧很火,像今年从《狂飙》到《漫长的季节》,都是口碑、收视、点击量都很好的作品。您平时会关注网剧市场吗?
陈宇:因为我以前早些年写过剧,近些年做电影会多一点,然后近期也在做网剧。我觉得网剧相对电影来讲,它能讲更复杂的故事,它的容量更大,也能体现我刚才讲到的叙事价值。当时我还跟艺谋一起做了个《坚如磐石》,里面有一些设计和想法因为体量所限没有在电影里面得到体现,然后正好腾讯来约,我们就做一个类似这样题材的东西。
院长:网剧市场可以挖掘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陈宇:对,我平常会看很多网剧,最近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黑暗荣耀》,我觉得写得挺好。包括前两年我比较喜欢的《信号》,也是韩剧。当然包括我们国内的《漫长的季节》我也非常喜欢。它所呈现出来的叙事的观念,以及对节奏的感受,以及它的这种趣味,我觉得都非常好。
院长:我觉得《漫长的季节》难得的就是很信任观众,中间观众一旦失去耐心很容易有口碑上的反噬,但是它一直撑到了最后一刻,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陈宇:对,其实它是具有很强的冒险性的,也有实验性。三个时空的非线性叙事,其实在主流电视剧里面挺罕见的。前面有几集,确实在其他地方做得非常优秀,于是把口碑给撑住了,不断有人作为自来水安利。它的高口碑和这种自来水的安利,帮它渡过了这个险滩,大家坚持到了中段以后,那么也就蹚过去了。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事,就是让观众接受的宽容度又打开了一次。
院长:不管是电影还是网剧,确实质量好的口碑也好,是不是也体现了这两年观众的审美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陈宇:这事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看得多就会好。看讲故事的方法多了,然后观众获取叙事信息的能力也在得到提升。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让观众看那种常规电视剧他压根就忽视了。那么现在观众,诶,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到后面又呼应了这个细节,他就觉得很爽。实际上是观众看多了各种各样的戏以后所培养的一个结果。当然也有很重要的因素是,电视剧观众逐渐年轻化,对于这个趣味的丰富和多元也就有了帮助。
院长:您刚才也提到《黑暗荣耀》,回过头看它剧本的技巧性特别高,我发现韩国的编剧好像特别擅长去塑造配角,特别擅长去写金句,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陈宇:也有很多人提到这个点,甚至延伸到对演员的判断,说人家的演员怎么都看着那么自然呢?你觉得这个演员非常好的时候,它就意味着这个片子整个做得好,整个工业体系是一个完善的结果。它不是说就我们中国的演员比他弱了还是怎么样,不是,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演员。韩国电影工业无论电影还是网剧,相对比较早地进入了商业化,它的体系化建设是值得我们是借鉴的。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创作的较好的势头,是综合因素,而非简单地说这个编剧会写,这个演员会演,还是一个系统化的东西。
院长:现在大家都习惯看短视频之后,可能有时候对于情绪的要求特别高,或者是对于节奏的要求特别高。
陈宇:这个不只是短视频,我们身处这个时代,信息的传输、交流速度和节奏会快很多。我们今天一个人获取的信息可能是 20 年前人的10倍。所以我们今天的作品也应该要适应这种新的心理结构和观众的阅读速度。那自然你在节拍上面会做一些变化,这个包括在我们创作中也会去考虑这个因素。
院长:除了有网剧的创作,最近还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陈宇:有电影的。我自己可能也会作为导演去拍一下,包括和艺谋导演我们肯定还是要继续往下合作。我这边今年想做一部青春片,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也是做导演的一部片,讲草根青年的一个青春片。
院长:您个人很喜欢青春类型吗?
陈宇:对。我觉得因为现在看电影的多为年轻人,而且今天的年轻人的生存样态和我们那个年代有很大的区别。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电影去鼓励他们,能够让他们寻找到自己的道路,能够让他们受伤的情感得到一些安慰,因为今天的年轻人确实不容易。当然大家都不容易了,中年人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年轻人更需要这种心理的理解和支持。
院长:大家一直对于国产青春片有一点偏见,就觉得好像没有拍出我们自己真正的青春,那您认为真正的青春是什么呢?
陈宇:因为很多青春片可能把爱情当成青春了,我觉得青春片的核心是成长。那么我希望做一个真正能够起到青春片这个类型意义的,它能够让我们看完后充满对生活的力量,能够得到一些心灵的安慰,能够更加勇敢地继续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无论在影视作品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间,如果大家能够给予青年一些理解、鼓励,我觉得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也想做一些这方面命题的作品。
院长:虽说网络很发达,社交平台看似年轻人都在发声,但其实年轻人是失语的。
陈宇:这个时代年轻人因为不占有舆论的主流,所以说他大部分时候无法撼动一些观念。就像你说的是一种失语状态。能够让他们说出话来,或者能够替他们说出话来,是特别重要的目标。
院长:还有一点,作为普通观众一直觉得我们的好剧本怎么那么少?您有没有计划培养一些年轻的编剧团队,带着大家一起搞创作?
陈宇:有。我现在想做一个青年的创作者联盟,一种沙龙式的定期聚会,大家会交流信息,包括社会心理的交流,包括项目的交流,包括我们帮助孵化作品,找大家一起来创作,希望能抱团取暖,形成青年创作者和产业中间的一个桥梁。
院长:我看到您马上也要去FIRST青年电影展当评委。您对青年创作者会有什么建议?
陈宇:我的建议就是,虽然创作本身是要有作者性的,是要有强烈表达的,但是我认为现在年轻创作者更缺的是在作者表达基础上,对于时代、社会、大众心理、产业样貌的一种认知。要想大众怎么想,其他的年轻人怎么想,其他的电影观众怎么想?你要去理解他们,要了解他们看一个电影、看一个故事的心理,要了解他们在这个时代最缺的是什么样的情感关注。去把自己放到这个土壤里面去。青年创作者更多是在关注自身的作品风格。但个性的东西还是要和这个时代,和普通人之间建立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