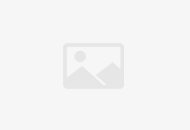【编者按】
2024年7月29日,在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中国游戏开发者大会(CGDC)“游戏音乐主题论坛”上,《沪游叙事·上海网络游戏产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沪游叙事》)进行发布。
《沪游叙事》由澎湃新闻旗下智库澎湃研究所主编,以详实的案例、一线的调研论证了“上海何以为重镇”,从产业纵深、发展切面、案例特写以及发展建议等角度出发,描绘上海网络游戏产业激荡二十年的发展图景。澎湃研究所将陆续刊发《沪游叙事》报告中的文章。本文为“案例特写”章节中的第三篇《世界主义:游戏中的群体文化自觉与个体精神连接》。
当意大利水管工马里奥风风火火地从红白机跳进中国家庭的客厅里时,电子游戏就已经搭乘全球化的风潮,开始成为最具跨时代特征的媒介。就像音乐、文学、电影,游戏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边界物(boundary object),能够穿越语言、种族、国别等固有的现实界限。
上世纪30年代,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游戏的人》一书中声明了游戏作为文化之母的世界主义内涵。他的比较语言学考据表明,游戏不仅是遍及不同地域社会的,更可以说具有文明的发生学意义。无论电子游戏与传统游戏的关系如何复杂,好玩的电子游戏必然或多或少地继承这一内涵,在角色设计、故事情节、商业策略的文化立场上兼容并包。
可能正是这种多层次的世界主义特征,让米哈游的重工之作《原神》获评有“游戏界奥斯卡”之称的The Game Awards (简称TGA )2022 “玩家之声”奖项。可以说,这款国产手游出海的商业成功,检验了世界主义在数字文化领域的重要性。
世界主义与本土情怀:《原神》的文化自觉之旅
技术生产力和美术雕琢是一款游戏走入国际视野的实力保证,而游戏所搭载的文化理想则是产生众多回响的关键。《原神》“提瓦特大陆”地图中的7个区域各有现实原型,经过“原学家”们在地貌、建筑、神话等方面的考证,人们看到了创作团队对每一类文化元素精细的美学与考古学还原。背景音乐尤其受到肯定,比如以古代中国为原型的璃月地区的背景音乐大量运用笛子、二胡等传统民乐;以中世纪中东、古印度和古埃及为原型的须弥地区的音乐用奈伊笛、乌德琴、曼陀铃等乐器。米哈游并不急于明确游戏国度与现实版图的对应关系,这种文化主义的处理方式也巧合地对应了一种开放的文明观:与分庭抗礼的民族国家政治体不同,在文化碰撞与传播中形成的文明体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在《原神》中跑图,就是在文化混搭中不断体验这种宽广的文明观,而故事情节的推进也不断引发玩家对战争与和平的反思。
实力与用心之外,《原神》也是在整个产销链条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手游之一。13种语言字幕,4国语言配音,在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同时兼顾国际玩家PC和主机的使用习惯,注重跨平台开发,游戏中的符号和图标设计考虑到了跨文化的可读性,使得不同背景的玩家更易接受和上手。《原神》的出海成功来自于对游戏市场全球化的充分认知:游戏不仅是一个静态的娱乐作品,更是跨文化交流的媒介。
若非在游戏内外兼具开阔视野,游戏原声《轻涟》不可能收获来自世界各地的共鸣。《轻涟》是《原神》游戏角色芙宁娜在司颂之章第一幕“水的女儿”中演唱的曲子。作为枫丹的前最高统治者,芙宁娜是水神“芙卡洛斯”的人类分身,她兼具人性与神性,歌声婉转动人,同时展现了她曲折的身世与复杂的人物性格。由于枫丹以法国为原型,这首歌请到了当时正在中国巡演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法国“国民级”女歌手希西莉亚·卡拉演唱,她同时也是一名《原神》玩家,这首歌一时间在法国社交媒体上引起讨论。据《文汇报》2023年11月的报道,[1]《轻涟》MV全球播放量超过1500万,动画视频、四位中国歌手演绎等多版本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8000万。动人的旋律和背景故事使得这首歌广受欢迎,有德国玩家希望在蒙德风神温迪的传说任务中加入德语歌曲,而日本玩家希望让稻妻国的八重神子唱段日文歌。
油管(YouTube)上掀起一阵轻涟风,非玩家网友也纷纷翻唱,歌曲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心灵连接在一起。有媒体评论道:“我们总说文化出海,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响当当的例子摆在眼前。回过头来看《原神》出海的成功,好像、似乎、也许、并非一定要用‘我们的’文化。文化,是需要沟通的,用他们的文化,讲我们的故事……这,是远比下载量、流水金额、在线玩家、会员数量更难能可贵的东西。”[2]
如果用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来概括《原神》的创作立场与推广策略,可以说是“文化自觉”。《原神》在美术、音乐、文学等多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与再创作,验证了世界主义和本土情怀在成功的文化输出中是一体两面的。1997年,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的理念,用以概括一个国家立于世界之林,面对21世纪全球化时应有的文化态度。这种自觉不是盲目的优越感,而是在对我们自身文化传统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形成对其他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包容态度,这一文化自觉至少包括三个层面:文化自信、文化尊重与文化交流,如此一来,才能够在世界上确认自己的位置,并与多元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3]从这个意义上讲,《原神》践行了这个重要的人类学理念。
另一扇世界主义大门:《风之旅人》的个体精神连接之旅
同样是旅人的设定游戏,早在10年前享有世界赞誉的游戏《风之旅人》(Journey)在获得好口碑的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商业成绩。在Play Station 3版游戏发售后,它马上打破销售纪录,成为当时北美和欧洲地区最畅销的Play Station Store游戏。[4]其标志性的游戏海报至今仍然出现在游戏设计的教科书、教学PPT和书籍封面上。
同样是旅行游戏,《风之旅人》与《原神》之间的划分在于创作意图的差异:一种以群体文化连接为中心的世界主义和一种以个体精神连接为中心的世界主义。
在《风之旅人》中,玩家扮演一位穿着红色长袍的神秘旅行者,目标是穿越荒野到达远方一座巨大山峰。没有文化包袱,也没有ARPDAU指标,这款游戏意境悠然,画面壮美,为进入世界的旅人提供纯粹的精神体验。没有打怪或与敌人无休无止的对抗,《风之旅人》让玩家意识到,旅行本身的冒险与挑战意义就已足够,有评论人将这种体验形容为一种超越言语的“无教派的宗教体验”。旅行者与观光者不同,观光者走马观花,旅行者探索未知,无需像买各种花式纪念品一样对符号资源占有和攀比,独自旅行的意义是直面自己。
这部作品之所以可以作为电子游戏跻身艺术行列的典范,不仅在于独特的东方禅意美学,还在于鼓励陌生人建立情感纽带的游戏立意:孑然一身的旅人会在路途中与同样穿着长袍的陌生人偶然相遇,虽然两人可以在旅途中相互帮助,却无法像其他游戏那样通过语音或文字交流,并且无法看到对方的名字。玩家间的唯一交流途径是没有词句的吟唱,这种吟唱会对游戏世界产生影响,使玩家可以通过关卡继续游戏。[5]这一没有“皮肤”,没有对话框,没有任何价值评判的朴素互动,让所有玩家感到了人与人之间在偌大世界中短暂陪伴的友谊与温暖。
超越传统游戏机制的情动(affect)是如何实现的?《风之旅人》在文化的兼容框架之外展示出另一种世界主义的可能:诉诸人类共有的精神追求与情感纽带。不必通过无限的文化蒙太奇扩大地图规模,也不用“氪”与“肝”来增加玩家的沉没成本,《风之旅人》能够成为经典,源于创作者个人的问题意识,这种强烈的个体本真性恰也具有世界性的感染力。游戏主创陈星汉出生于上海,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之后去往美国读书,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That Game Company,他的作品自然显露的东方意境,也让他被称为“游戏禅师”。陈星汉曾在机核网的一次访谈中谈到,自己试图通过没有特征(性别、外貌、声音、语言等)的设定实现去标签化的社交。在个人经历中他曾感受到标签化的社交排斥。刚到美国时的语言不通、文化隔阂、经济压力等都让他在留学过程中倍感孤独,即使在《魔兽世界》中最初可以凭借技术获得其他玩家的好感,但是当对方听到他的亚洲口音就不再跟他交流。[6]
“我开始思考,有没有这样一款游戏,大家穿着袍子,里面所有人的性别是模糊的,年龄也是模糊的,人和人之间互相沟通互相交流,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一个亚洲人和一个美国人、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的关系。”[7]他希望能有一款游戏,能够真正地跨越语言,种族,外貌,把纯粹的人类同胞连在一起。《风之旅人》能做到,如人类学家项飙所说,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结果,自主的自我意识也最具超越自我的潜能,从而真正是世界性的。对孤独的共鸣反过来温暖了孤独的个体。
电子游戏或多或少都是将一段时空压缩在某个独立的世界中,无论是《原神》,还是《风之旅人》,所有玩家都是这个“异国他乡”的陌生人。电子游戏在开放世界方面的玩法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还原游戏世界主义全貌的过程,更是突破竞技游戏观的一种尝试:游戏的乐趣可以是探索未知和沟通彼此。肩负起文化自觉的“重担”之外,从个人本真的感知、对“附近”的思索出发,也许是中国游戏通往玩家心灵深处的另一扇世界主义大门。
赫伊津哈曾哀叹欧洲进入现代之后游戏精神的衰落。在他悲观的文化衰败反思中,“虚假的游戏”假以游戏之名,制造了精神平庸的个体、加剧了不同商业与政治群体之间的竞争。赫伊津哈发现了文化创造与人性发展的潜能也蕴含在游戏冲动中,但也将这种本能视为极易被利用和被污染的。中国的游戏制作与消费市场无疑正在面对这种挑战,“氪”与“肝”早已成为游戏创新的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