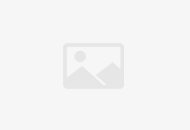关于魏晋玄学发展历史史
就理论层次而言,玄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那关于魏晋玄学发展历史史是怎样的呢?
玄学作为一门学问,简言之是处理自然和名教的关系。
儒家贵名教,道家法自然,因而如何协调儒道使之能更好的为现实服务成了玄学家们的执着追求。
自东汉末年以来,由董仲舒创立的天人感应的经学已无法调和社会矛盾,所以人们基于这个事实进行了不断探索,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首创贵无论。
之后历代玄学家们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到玄学研究中。
他们围绕这个话题所阐述的独特见解,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一种冷静的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一种热烈追求。
在那个悲苦的年代,他们站在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理想的高度来审视现实,试图去克服自由与必然,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背离,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转化为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否结合的玄学问题,无论他们对这个命题是持肯定还是否定,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表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就理论层次而言,玄学家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
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根据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对儒道之所同作了肯定的论证,这是正题。
魏晋禅代之际,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崇道而反儒;西晋初年,裴頠为了纠正虚无放荡之风以维护名教,崇儒而反道,于是儒道形成了对立,这是反题。
到了元康年间,郭象论证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把儒道说成是一种圆融无滞体用相即的关系,在更高的程度回到玄学的起点,成为合题。
从思辨的角度看,合题既高于正题,也高于反题。
玄学自此告一段落,其后虽有东晋的佛玄合流,因为篇幅所限且其以佛家为主,玄学为辅,略去不论。
郭象虽然作为玄学的集大成者,但他那套理论并没有真正解决儒道会通问题。
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理论的逻辑并不一定能推演于现实中。
八王之乱和石勒之乱的接连发生把他刚刚出炉的理论碾了个粉碎,从而使名教和自然重新陷于对立。
这也表明,玄学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在此之后,虽然清谈放荡之风仍在世家大族中盛行,但求真务实之风正在庶族中兴起,最终在隋唐之际埋葬了玄学,代之以佛家的清静无为。
至此,玄学连一种个人修养都算不上了,更不要说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贯彻执行了。
我们讲玄学,就如欧美研究拉丁文一样,学术价值大一些,现实意义已被抹去的差不多了。
正式玄学: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
我们今天研究一位哲学家,主要应该着重于他的著作而不是生平。
因为著作是他思想的记录,是他把自己的个性完全融化在普遍性的结局,也是他之所以成为“理性思维的英雄”的本质所在。
而生平则不过是体现了他的非本质特征,一种无法超越的特殊的境遇。
关于何晏王弼的生平略去不论,总之暗淡无光。
但是他们独创性的思想却影响深远,甚至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玄学思潮,完全有资格配得上黑格尔在《哲学讲演录》导言中说的“理想思维的英雄”的称号。
在贵无论玄学的建立过程中,何晏作为倡导者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他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汉代神学目的论和元气自然论的本体论的哲学思想。
例如他在《道论》说:
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
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
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之以黑,素之以白,矩之以方,规之以员。
员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
“有之为有,恃无以生”,这个命题承袭了汉代宇宙生成论的传统说法,而以“无”作为“道之全”则是玄学独创性的命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宇宙生成论到玄学本体论的关系。
何晏及后来的王弼都特别强调天下殊途同归,百虑而一致,他在解释孔子的“予以一贯之”时说:
善有元,事有会。
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知其元,则众善举矣。
故不待多学,而一知之。
(《论语集解·卫灵公章注》)
为了适应玄学初创的需要,何晏着力于确立本体比现象更为根本的观点,因而把圣人的人格提到半人半神的高度,和常人完全对立,以致于它最杰出的弟子也不能理解。
在谈论本体时却遗忘了现象,在谈论现象时又丢到了本体。
再解释《老子》上,只是把纷然杂陈的众多现象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无。
这就既不能圆满解决贵无论玄学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也无法全面解释,《老子》。
还有他因为“不解《易》九事”没有写出关于《周易》的著作,屈服于象数派易学。
尽管何晏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贡献还是主要的,并且值得现代人学习的是他豁达大度虚怀若谷,把未完成的'工作真诚地让给王弼去做。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
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之论》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
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
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这两条记载,一云“始成”,一云“未毕”,但都表明,何晏却是由衷的承认自己对《老子》的理解比不上王弼,而甘拜下风。
在中国学术史上,能够具有何晏这种真正学者风度的人,大概并不是很多。
由于何晏的解释存在偏颇,也未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历史便把这个工作交由王弼继续完成。
王弼的解释学的基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周易略例》和《老子指略》这两部著作中。
王弼在《老子指略》说:
《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
噫!崇本息末而已矣。
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
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
解其一言以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位意,则虽辩而愈惑。
然则《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
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
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己;此其大要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弼对《老子》的理解为“崇本以息末”,比何晏的“以无为本”更进一步。
王弼解释《周易》所依据的原则集中表现在《明彖》和《明象》中。
他在《明彖》中所提出的“以寡治众”,“以一制动”,“统宗令无”,“约以存博”,“简以济众”,从思想实质来看,和他解释《老子》所遵循的“崇本息末”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着眼于解决本体和现象的关系。
在《明象》中,他指出,“言生于象”,“象生于意”,“意以象若”,“象以言著”,在“言”(封爻辞),“象”(封爻象),“意”(意义)三者的关系中,意义是第一性的,所说的“意义”指的是思想,关于人事的智慧。
王弼的这种本体思维同时也就是他的解释学思想。
大体上说,由于《老子》原文偏于说无,王弼在解释它时着重于由体以及用;《周易》原文所谈的是六十四卦的卦义,属于有的范畴,王弼则着重于由用以求体,致力于发掘其中本体论的哲学意义。
通过王弼这种新的解释,《周易》和《老子》的矛盾得到顺利解决,形成了一种有无互补的关系,在贵无论玄学的理论基础上获得有机的统一。
但是王弼的玄学体系有和无仍分为两部分,只得到了外部的松散联结,而没有达到紧密联合的水平。
无与有的对立,逐渐扩展为崇有和贵无两种理论形态的直接尖锐的对立。
裴頠提出的崇有论标志着王弼贵无论玄学体系的正式解体。
由于他的本体论尚未达到“体用一如”或“体用一源”的高度,把有无分为两部分,名教与自然也仅仅只做到了外部松散的联结。
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和裴頠的重名教而轻自然的思想便是王弼体系矛盾的外在化,也同样是一种逻辑的必然。
竹林玄学:阮籍嵇康的自然论玄学
玄学到了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打折名教的旗号,罗织罪名,诛锄异己,把名教变成残酷毒辣的权力争夺工具。
人们被迫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做出选择。
表面看来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拥护司马氏政权的选择了名教,反对派则选择了自然。
同时儒家贵名教,道家法自然,这也是对儒道两家思想的选择。
其实,从深层的含义来看,这种选择反映了魏晋禅代之际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人们或者放弃理想与现实妥协,或者坚持理想与现实抗争。
阮籍嵇康的思想也由前期的儒道结合到崇道反儒,遵循了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方向,但是由于现实世界的自我分裂和二重化,他们的玄学思想不能不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演变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
玄学思想的发展是在既同世界对立又同世界统一的矛盾中进行的。
就本质而言,玄学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它力求与世界协调一致,为当时不合理的政治局面找到一种合理的调整方案。
但是当现实变得更不合理,连调整的可能性也完全丧失时,玄学从世界分离出来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实不合理的存在。
玄学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给自己披上了一层脱离现实的玄远之学的外衣,由政治哲学变为人生哲学,由外向变为内向,由积极入世变为消极避世。
虽然如此,由于哲学归根到底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哲学不可能脱离现实,正如人们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所以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一直是承担着巨大痛苦,在对立的两极中动荡不安。
他们把外在的分裂还原为内在的分裂, 并且极力探索一种安身立命之道来恢复内心的宁静,为的是使世界重新获得合理的性质,在更高的层次上适合人们的精神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阮籍嵇康思想的演变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逻辑的必然。